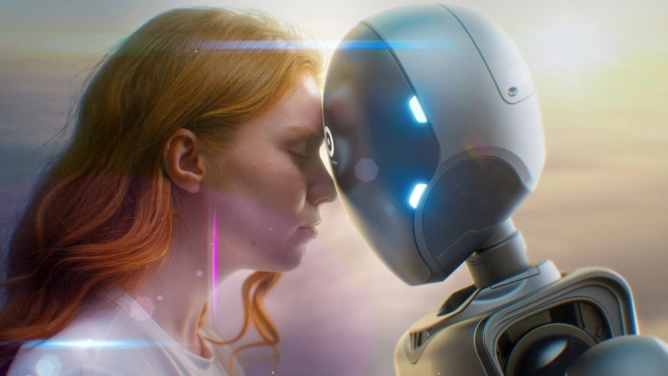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哥本哈根将融入转变为个人合同,其中对可持续居留和公民身份的获取取决于就业、语言能力和公民合规性。根据Wilfried Martens欧洲研究中心研究员Lucie Tungul的分析,这种方法代表了“社会凝聚力与自由开放之间的政治妥协,其中融入成为个人责任,而非集体包容”。
连续的改革,从限制家庭团聚到减少社会福利,稳定了国内政治共识,并减少了对极右翼的支持,但也产生了模糊的社会效果。
丹麦重新定义了融入的概念,将其从集体责任转变为个人义务。从2010年开始,获得永久居留权和随后获得公民身份的条件是证明“成功融入”,通过积极参与社会、语言能力和就业来衡量。每位移民签署一份个人融入合同,承担具体目标,由市政府进行监督。评估通过一个积分系统和“积极公民身份”测试进行,不仅包括语言和职业能力,还包括遵守丹麦的公民价值观——民主、性别平等、言论自由和宗教宽容。
与此同时,2001年后通过的改革直接将工作权和自我维持的权利联系在一起,显著减少了对非欧盟移民的社会援助。随着2019年所谓的“范式转变”,重点从长期融入转向自愿回归:难民身份变为临时,社会福利转变为“自我维持或遣返援助”,最高可达5400欧元。拒绝回归的人被安置在特殊中心,没有财政支持。这些措施的许多实施得益于丹麦在欧盟共同庇护政策中的选择退出,这使得政府在欧洲拥有独特的操作空间,但也增加了对欧洲法律的责任。
根据Tungul引用的数据,到2024年1月1日,移民及其后代占总人口的16%,其中10%来自非西方国家,6%来自西方国家。罗马尼亚人约占丹麦移民及其后代总数的5%,仅次于土耳其和波兰。MENAP和土耳其群体的就业率为60%,而其他非西方国家的就业率达到71%。这些群体的女性就业率仅为53%,然而在丹麦出生的下一代就业率达到73%,这表明融入过程缓慢但真实。
在1986年至2016年间,移民法被修改了118次,这在欧洲是前所未有的频率,显示出一个持续适应政治和社会压力的立法过程。
Lucie Tungul指出,丹麦的方法成功地通过主要政治力量采取共同的限制性政策来减少对激进党的支持。社会民主党甚至继续加强立法,明确表示“零庇护申请”。然而,研究者强调了成本:“基于威慑的融入可能导致没有归属感的适应,缺乏公民包容感的经济参与。”在丹麦人和非西方移民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就业、教育和社会流动差异,而临时难民的法律不安全感加剧了临时感。
领土分散政策被视为一种行政成功,但并未阻止非西方移民集中区的出现,这导致了最初被称为“贫民窟法”的法律的通过。在目前的形式中,重新命名为“平行社会法”,这些规定正在接受欧盟法院的调查,以确定是否存在基于民族来源的歧视。Tungul指出,“这些措施可能与欧盟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特别是在居住和社会混合的评估方面”,这一问题可能对其他成员国的城市政策产生影响。
根据作者的说法,丹麦模式提供了双重教训:高效的行政、向市政府的去中心化和对工作的重视是可复制的元素;然而,基于威慑和条件的融入可能会产生长期的排斥效果。“丹麦的政治成功是无可争议的,但仍需观察这一模式是否能确保一个凝聚和可持续的社会,”Tungul在结论中写道。
在丹麦的罗马尼亚社区,估计约占总移民的5%,以经济和融入为主的特征突出,基于工作和职业流动。与受到限制措施影响的非西方群体不同,大多数罗马尼亚人从事建筑、物流、农业和服务等行业,直接为丹麦经济做出贡献,并享受欧盟公民身份所保障的自由流动。这种自我维持的导向使他们被地方当局视为一个受欢迎的类别,地方当局对待他们的行政方式与对待难民或非欧洲移民的方式不同。